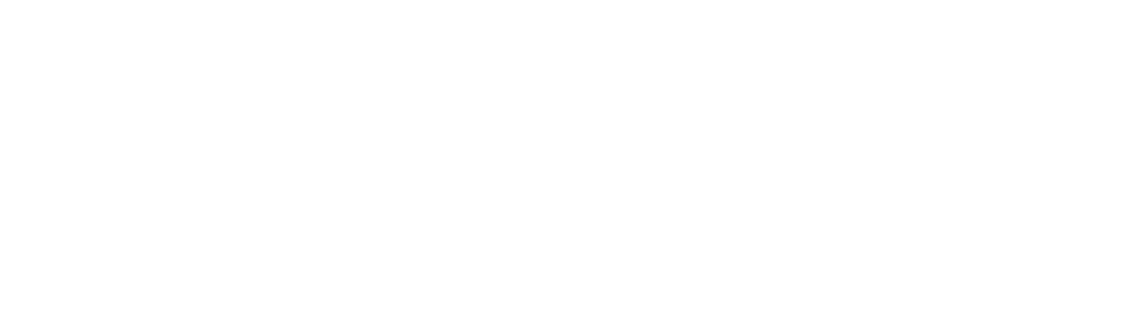概念史研究的文化意蕴
1972年《历史性基础概念:德国政治—社会语言历史辞典》第1卷问世,1997年最后一卷第8卷出版,这期间概念史研究在德国以外产生了不同的反响。1985年,科塞雷克的重要论文被结集英译为《过去的未来——历史时间的语义学》(Futures Past■★◆◆: On the Semantics of Historical Time)出版◆◆★◆★,这本对概念史旨趣进行阐释的论文集受到海登·怀特的推崇■★◆■★,他称科塞雷克为20世纪最重要的历史理论家之一■■◆。但是◆★,在法英两国,概念史的境遇不佳。师从科塞雷克的法国学者阿赫多戈称概念史在法国被无视■★■,是“不敢说出自己名字的思想史”。英国政治思想史家斯金纳甚至直言没有概念史,只有围绕概念争论的历史。政治思想史家波考克质疑以概念而非语言或话语作为研究对象的可行性。来自法英的冷淡或批评表明彼此之间存在学术理路的歧义,英国政治思想史的“语言”研究要在经验■★◆■,法国的■★“话语”研究重在实践,而概念史关心的是“概念”长期的历时性变化★■★★。
德国哲学家伽达默尔说◆■:“语言并非仅仅是指称对象整体世界的符号系统。语词并非仅仅是符号■■。在某种较难把握的意义上,语词几乎就是一种类似摹本的东西。”(伽达默尔◆■:《真理与方法》(一)■★★■■◆,洪汉鼎译,商务印书馆2017年版★★★★■,第586页)学术研究的展开离不开对词语内涵的梳理■◆◆★,概念史研究之所以重要,源自其一个基本信条——概念即历史■◆■★◆,也即概念不只是认识历史的方法★★■■◆,其本身就蕴涵着历史和文化的符码◆■◆★■。
但是★■◆◆★,即使在方法上趋近了,仍有不可逾越的历史和文化沟壑——不同语言之间概念的“可译性★◆”或◆★◆★“互译性■■”问题。在欧洲语言中也存在如何翻译的难题★◆■◆★。以色列历史学家范妮亚·奥兹-扎尔茨贝格尔研究18世纪末苏格兰道德哲学的德文翻译后,发现译者用德文Staat(国家)翻译英文Community(共同体)◆◆★■、Polity(整体)和Nation(民族),致使后者失去了在苏格兰文本中蕴含的古典共和主义的意味◆★◆,更为糟糕的是,颠覆了苏格兰文本内涵的批判性◆■★■■★。斯坦梅茨回忆20世纪80年代末在比勒费尔德大学参加科卡和韦勒领导的重大研究项目——从比较角度探讨现代和当代欧洲的Bürgertum(资产阶级、市民阶层),最后他们发现以几乎无法翻译的Bürgertum作为研究出发点的错误,因为以这种方式开始研究,一开始就预示着存在德国“特有之路”(Sonderweg)。
科塞雷克在给该辞典撰写的导言里◆■★,揭橥了概念史研究的基本内容■■■,概言之★◆■★◆,一个概念要成为历史性基础概念大致需要满足四个标准:民主化■★★■、时间化、政治化和意识形态化。民主化即社会化或大众化,指原来由贵族、教士等垄断的知识逐渐为普通人所掌握。时间化不是指外在的时间,如自然时间和纪年等★■◆◆★★,而是指概念本身所内聚的过去的经验和未来的期待,正是在这二者的张力中概念才得以成为近代或现代概念。概念一旦为不同团体、党派所使用,即开启了政治化的进程。政治化的概念有可能意识形态化——抽象化,抽象化的概念与其实际之间必然产生张力■◆■★。
上述发生在欧洲的翻译问题■◆,在意欲研究19世纪以来的近代新名词和概念的东亚同样存在。在科塞雷克访问日本二十余年后,中国、韩国和日本兴起了概念史研究。这些地区同属汉字文化圈★◆★,汉字对译西语为比较概念史研究提供了难得的范本◆★◆。就中国而言,在讨论由词语和概念建构的近代时,既要关注汉字译词与西文的关系★■◆,还要兼顾来自日本的影响◆◆★★,由日本转译的多是由具有丰富汉学知识的学者提出的,之所以为晚清知识人广泛接受■■◆■◆★,乃是因为彼此在语言文化上有着互通之处◆★◆◆。无疑,汉字概念与西文概念不可能完全对等,即使同样使用汉字概念的中日韩之间也存在巨大的差异,比如西文的Gentry,在中文被视作士绅,日文为“大百姓”◆★■■,韩文是“两班★★★◆■★”,细究起来,它们之间存在不可互译性,语义表现为一种社会结构★★◆★◆,各自对应的社会结构各不相同。更不必说◆■,翻译概念在达成译词的标准化和广泛使用过程中★★■,与政治■■◆、社会之间产生的互动和互相再造的关系了◆★◆◆■。
斯坦梅茨在批判“欧洲中心主义”时,指出反映西方世界观的诸如“政治”◆◆■★“宗教”“社会”“个人”等概念已经深深嵌入非西方社会,而非西方社会的历史学家、民族学家和文化专家常常通过在其叙述中插入所观察的行为者的术语来消解外来性问题,这产生了一种消灭欧洲中心主义的错觉。实际上,去欧洲中心主义是为了对抗权力的压抑,而非将外来的翻译语和概念弃之不用。在笔者看来,全球本土化的概念史研究旨在深究特定情境下概念的生产和再生产及其结果,与此同时,在深化研究中建构自己的“话语体系”◆■◆★■,是我们努力的方向。
面对概念史受到的质疑,科塞雷克的弟子■■◆、比勒菲尔德大学教授斯坦梅茨提出应该将视线下移到十九世纪末以降的★★◆◆“高度现代性■◆★■”的时代,同时加强对概念与反概念、相邻概念、语言表达和隐喻等的研究■■★■★★。有鉴于概念史虽然描述了语义变化而缺乏有效的解释力,他在《历史语义学:理论问题与研究实践》一文中认为,历史语义学有必要来一次◆◆“经验性转向”,展开微观层面的历时性研究。在他看来,语义学的核心问题是语言和语言之外“现实★◆★◆”之间的关系,也即如何将语言之外的■◆★★■◆“现实”和过往由语言形成的★★“事实”概念化。借用卢曼关于语义的定义——暂时稳定的言说和书写方式,语义可以制度化和仪式化。如此一来◆■★◆■★,关于语义学的定义多少都与◆◆◆★“社会结构◆■★■◆◆”有关★■◆。事实上,与社会结构一样,语义由个人行为(语言行为)构成◆◆■■★,对行为者既是约束也是动力,历史语义学或历史话语需要建立一种解释语义变化的模型,进一步追问语义何以产生■◆★、消失以及不断变化。
概念史起初是一种哲学辞典的编纂方法。黑格尔去世后出版的《历史哲学》出现了一个特别的用法,将历史书写分为三类——“原始的历史”★★◆“反思的历史”和“哲学的历史”◆■★◆■,“概念史”被归入■◆★■■◆“反思的历史”★◆■◆。因为只有孤例★★◆★,且黑格尔没有阐释何谓概念史,因此有人怀疑这里的概念史是否出自黑格尔之口★◆■◆,抑或为记录者所误加。但是■★,这一用法别具意义,被赋予感知和反思意涵的概念史不正是科塞雷克、布鲁内尔和孔茨等主编《历史性基础概念★◆:德国政治—社会语言历史辞典》所要彰显的旨趣吗?正是在这部8卷(第9卷为索引)大开本的历史辞典中,作为理解和反思的概念史被确立为一种书写历史的方法。需要赘言的是★■★◆★,这里的“历史辞典■◆■■■◆”(Historisches Lexikon)虽有一般辞典的书写规范★■◆★■,但是内容异于通常意义的辞典词条■★★,有的概念篇幅堪比专著。